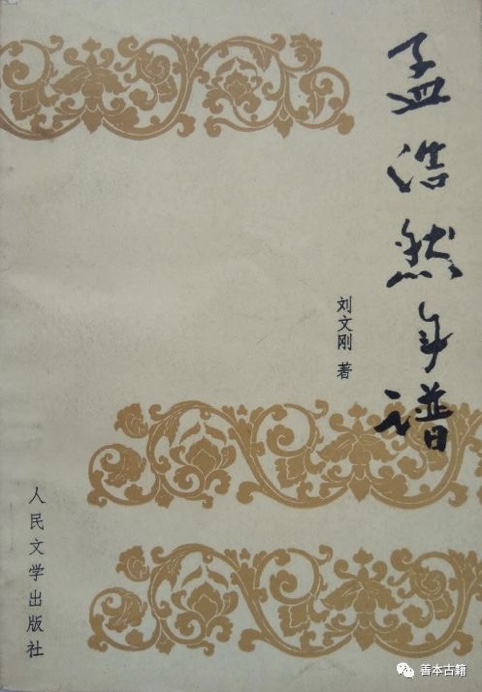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文刚《孟浩然年谱》(以下简称“《年谱》”),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及部分作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系年,有助于人们对孟浩然其人其作的具体把握与理解。但是,《年谱》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。因此,本节特就其中之具有代表性者,略作考辨与订正。
一、张子容进士及第的时间。

张子容是孟浩然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交游之一。《年谱》于景云二年内以“按”的形式写道:“考张子容为先天二年进士,先天元年应为其准备应举和赴举时间……”又于先天元年内云:“冬,送张子容应进士举,有诗。”并有“按”云:“唐进士于次年春应试,头年冬集于京师。张子容为先天二年进士,又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,襄阳距长安一千一百馀里,张子容赴举应在本年冬,浩然送别亦应在冬天。《登科记考》卷五认为本诗(指孟浩然《送张子容赴举》诗——引者注)作于开元元年,显然失考。”又于开元元年系张子容进士及第于是年,并说:“《唐诗纪事》载张子容为进士时间(在先天二年,即开元元年,是年十二月改元——引者注)无误。《唐才子传》及《登科记考》言张子容为常无名榜进士亦不误,唯登第时间误早一年。”
按:《年谱》在上述三年(景云二年、先天元年,开元元年)内所涉及张子容进士及第事,乃均不的。首先,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五考订孟浩然《送张子容赴举》诗在景云三年亦即先天元年(是年八月改元),而不是如《年谱》所言为开元元年(此误应为《年谱》作者误读《登科记考》所致)。其次,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与《登科记考》之“唯登第时间误早一年”者,并晨事实。其三,《登科记考》卷五据常衮《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墓志铭》一文,考订常无名与张子容登第时间均为先天元年,乃属正确,《年谱》认为“常元名拔萃登科之年即进士擢第之年,故常无名为先天二年(开元元年)进士无疑”的说法,则为错误。对此,傅璇琮主编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一《张子容》系张子容进士及第在先天元年的事实,又可佐证。所以,张子容进士及第时间之正确者,乃为先天元年,而孟浩然《送张子容赴举》诗的作年,则乃在景云二年。
又,《年谱》认为张子容赴举在先天无年冬天的说法,亦误。考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十八《诂笺三》“进士科故实”云:“举场每岁开于二月。每秋七月,士子从府州觅解纷纷,故其时有‘槐花黄,举子忙’之谚。”[1]又徐松《登科记考凡例》云:“其应举者,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,生徒亦以十月送尚书省,正月乃就礼部试。” [2]综此二者,知作为“乡贡进士”的张子容自襄阳始程赴京应试之时间,是必在当年秋天而非冬天的,否则,其即难以“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”。《年谱》作者因不谙此,而作想当然之推测(指毫无文献证实而认为“张子容赴举应在本年冬,浩然送别亦应在冬天”),实则谬不堪言。
二、孟浩然开元九年未曾游洪州。
《年谱》在开元九年内说:“(孟浩然)游洪州,九月九日在长沙有诗寄刘大眘虚,至晚应为本年事。”并云:“游南康之赣石、落星湾,至晚也应在本年。”又说:“初到浔阳,作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诗,应在本次游洪州、南康之时,或作于本次之前。”由是,在“系年诗”内,将《九日于龙沙作寄刘大眘虚》、《下赣石》、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三诗,乃皆系于开元九年内。
按:《年谱》之所以认为孟浩然在开元九年内游洪州,所据为二:其一是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一《刘眘虚》之所载;其二为本年“系年诗”中的上述三首孟诗。实则此二者均不能作证孟浩然的洪州之游,乃在开元九年。据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一,知刘眘虚开元十一年进士及第,《年谱》依之乃认为刘眘虚入京赴举在开元十年,并说:“故浩然寄诗,至晚应为本年。他们成交,自然又在寄诗之前。”按孟浩然所寄之诗,即其集中的《九日龙沙和作寄刘大眘虚》:“龙沙豫章北,九日挂帆过。风俗因时见,湖山发兴多。客中谁送酒?棹里自成歌。歌竟乘流去,滔滔任夕波。”第一句诗明确告知我们,浩然此诗乃写于豫章之北的龙沙,则孟浩然曾游洪州者,即可遽断。虽然如此,但此诗并不能证明孟浩然之游洪州乃在开元九年,这是因为,《年谱》无只字与此相涉,其“开元九年”说又何令据信?更何况,孟浩然开元九年乃在湖湘至岭北一带寻访友人袁瓘[3],根本不曾有过洪州之行。另,《唐才子传》卷一《刘眘虚》载刘眘虚开元十一年徐征榜进士者,亦不的,原因是一则《唐才子传》卷二《刘长卿》谓刘长卿“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”,另则《登科记考》卷七开元十一年、卷八开元二十一年之进士登第者,均无刘眘虚名(另可体参见傅璇琮主编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一《刘眘虚》)。如此,则《年谱》认为刘眘虚开元十年入京赴举的说法,即成为了缘木而鱼。又,除《九日龙沙作寄刘大眘虚》一诗外,被《年谱》编于开元九年内的《下赣石》、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二诗,亦未能举出只字以为证实,纯为作者的自说自话。所以《年谱》系孟浩然开元九年之游洪州,乃纯属臆测所致,未可据信。
三、孟浩然与李白江夏相会的时间。
《年谱》在开元十三年内系“李白出蜀,游洞庭襄汉”,并认为“浩然与李白成交当在本年”。于开元十四年内则云:“三月,浩然游扬州,途经武昌,路遇李白。李白于黄鹤楼作诗送行。”
按:《年谱》此之所系,乃大误。这首先表现在孟浩然与李白初识之时地并非为开元十三年的“襄汉”。《年谱》之所以作如是认为,一是据清人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中的“开元十三年(指开元十四年——引者注)已称浩然为故人,故二人成交当在本年”。实则此二者皆不的。李白出蜀后首游“襄汉”,乃系由扬州、金陵一线逆江经江夏、安陆而至,其时在开元十四年秋,对此,拙著《李白求是录·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》一文,已有详考,此不具述。而实际的情况是,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于开元十四年夏秋之维扬,对此,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、拙著《李白史迹考索·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》等,亦均有详考,可参看。所以,《年谱》认为孟浩然与李白“成交”于开元十三年的说法,乃是一种毫无文献依据的错误说法。
又,孟浩然一生曾三游越剡,其具体概况为:第一次为开元十三年春至开元十五年夏,始程地为襄阳;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秋至开元二十二年夏秋,始程地为洛阳;第三次为开元二十三年春至当年冬,始程地为襄阳[4]。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自襄阳始程时,李白尚在蜀中(孟浩然开元十三年三月离襄,李白于是年五月顺长江出峡),而开元十四年的三月孟浩然已在维扬一线漫游,其又怎么会在武昌遇李白于黄鹤楼呢?而综观孟浩然一生的三次越剡之游,知李白在武昌写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替孟浩然送行者,只能是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孟浩然第三次游越途经江夏之际。这是因为,孟浩然第二次游越剡乃是首途于洛阳,此即著名的“自洛之越”。开元二十三年,孟浩然三游越剡有下列两项材料可确证:其一是孟浩然集中的《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》、《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》二诗;其二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八对崔国辅“应牧宰举”的记载。孟浩然《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》诗有云:“春堤杨柳发,忆与故人期。”《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》诗则谓:“我行穷水国,君使入京华。”合勘二者,知孟浩然在某年春天,因应山阴少府崔国辅之“期”约而曾东游越剡一次,待其至山阴(今浙江绍兴)时,崔国辅已先此西入长安了。据《登科记考》卷八的记载,崔国辅是次之由山阴至长安,乃是因为“牧宰举”所导致,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春,则上引孟浩然的两首诗均写于开元二十三年春者,即足可论断之。孟浩然此次因应崔国辅之“期”而东游越剡,在途径江夏时再会李白于黄鹤楼,故李白乃写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以替其送行[5]。
综上可知,孟浩然与李白江夏相会的时间,其正确者应为开元二十三年,而非如《年谱》所言之开元十四年。
四、关于孟浩然入长安的时次。
《年谱》在开元十五年内云:“冬,浩然赴进士举往长安,途中遇雪,有诗咏之。”并在“按”中说:“浩然入京,一次为本年,一次为开元二十二年。而后一次可以确定不是冬天入京,故诗(指《赴京途中遇雪》一诗——引者注)作于本年。”又,《年谱》在开元二十二年内云:“浩然再上长安求仕。”并在“按”中说:“浩然再上长安的具体时间失载。考丁凤去年(指开元二十一年——引者注)入京时,浩然尚未决心上长安。而明年韩朝宗举荐时,浩然不赴荐,说明他已上长安求仕而未遂。因此,浩然上长安求仕在本年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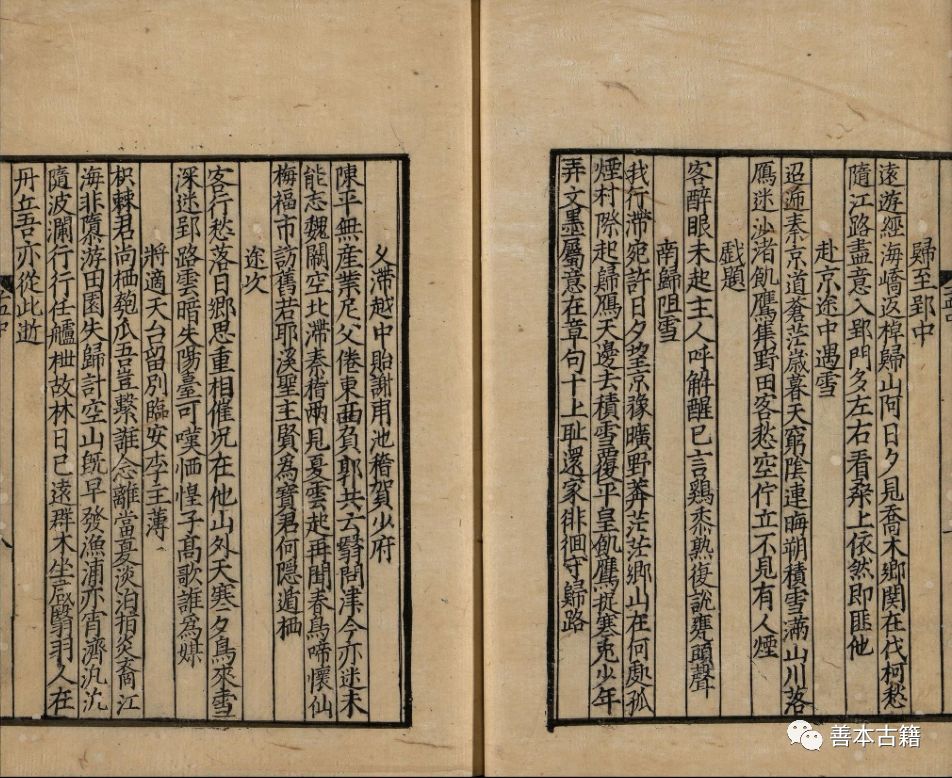
按:《年谱》所系孟浩然开元十五年与开元二十年的两次入京,均与史实不合,故乃全误。先看开元十五年的一次入京说。《年谱》认为孟浩然是年入京的唯一证据,便是其集中的《赴京途中遇雪》一诗:“迢递秦京道,苍茫岁暮天,穷阴连晦朔,积雪满山川。落雁迷沙渚,饥鹰集野田。客愁空伫立,不见有人烟。”但检两《唐书·玄宗纪》、《五行志》可知,开元十五年冬天的“秦京道”根本无下雪之载,则是诗非作于开元十五年冬者,即可肯定。而事实上,此诗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一年因张说之荐而奉诏入京时所写。开元十一年,张说“正除中书令”,大权在握,而其平生中喜识拔后进,且其此前又与孟浩然私交甚密,故其在“正除中书令”后,即将孟浩然推荐于唐玄宗。对此,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三乃有记载:“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,令诵所作。”[6]而《旧唐书·玄宗纪上》于开元十一年内又恰好有是年京秦一带下过一场大雪的记载:“是月(十一月),自京师至于山东,淮南大雪,平地三尺馀。” [7]诗史互印,事实确凿。
再看开元二十二年的二入长安之说。《年谱》认为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二年曾二入长安者,无任何材料作依据,纯属作者之自说自话所致,故其实不值一辨,兹罢论之。至于其将《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》、《闻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户除豫州以投寄》二诗分别系于开元二十一年与开元二十二年的作法,亦属错误。《年谱》系前诗于开元二十一年的理由,主要是认为是年张九龄已“执政”即“正式拜相”。但《年谱》作者却不知孟浩然与张九龄相识乃在开元二十五年的荆州长史府,对此,拙作《孟浩然结“忘形之交”考》一文[8],已有详考。此为其一。其二,从现存孟浩然集中记载孟浩然与张九龄过从之诗可知,孟浩然于诗题中皆称张九龄为“丞相”,而此诗题则直呼张九龄名讳,此显然与前者不符。这一实况表明,此诗题末的“呈张九龄”四字,当为后人所妄知,而宋蜀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无比四字者,又可为之佐证。如此,则《年谱》的“丁凤去年入京”云云,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材料。至于孟浩然在襄阳的“不赴荐”,所表明的是他对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,而非“说明他已上长安求仕而未遂”[9]。裴朏其人,据《全唐文》卷三九○独孤及《权公神道碑》一文可知,其开元十八年前即已在长安为“学士”,开元十八年则与李宙等人应诏考校书判甲乙丙丁科,如此,则其又焉可在开元二十二年“自襄州司户除豫州司户”呢?更何况,据王溥《唐会要》、岑仲勉《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》等可知,裴朏自以怀州司马衔入京为“学士”后,乃官礼部郎中直至天宝二年,其间他根本不曾被贬外出。所以,此诗的正确作年,乃为孟浩然首入长安的开元十二年秋七月[10],而非为《年谱》所系为开元二十二年。
五、《秦中苦雨》诗的作年。
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孟浩然集》卷二有《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》一诗,《年谱》将其作为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“冬,离开长安”的一条主要证据主要证据,故于“按”内说:“《(答)秦中苦雨思归而(赠)袁左丞贺侍郎》诗云:‘去矣北山岑’,意即要回故乡襄阳。诗作于九月。浩然在长安有不少友人,又值秋霖,不会九月就离开长安。但以浩然当时愤激的心情而论,也不会逗留很长时间。略事盘桓,离开长安显然在冬天。”并将此诗在“系年诗”内系于开元十六年。
按:《年谱》此系实属错误。这是因为,如上之所考辨,孟浩然在开元十五年根本不曾到过长安,因之此诗之作年非在开元十六年者,即甚为明白。为使这一说法更为显豁,兹另作考辨如次。按孟浩然集中有《送辛大不及》一诗,表明开元十六年秋七月前的孟浩然乃在襄阳。是诗有云:“送君不相见,日暮独愁绪。……郡邑经樊邓,山河入嵩汝。蒲轮去渐遥,石径徒延伫。”诗题中的“辛大”,即孟浩然的乡友辛之谔(孟浩然集中另有《西山寻辛谔》、《都下送辛大之谔》等诗,其中的“辛谔”、“辛大之鄂”,均乃辛之谔之讹),据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七,知其开元十七年因上《叙训》二卷而授长社尉。又据上引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十八《笺诂三》“进士科故实”与徐松《登科记考凡例》所载,可知唐代士子进京应试乃始程于先一年的秋七月,以此勘之辛之谔开元十七年上《叙训》而授长社尉的史实,则其自襄阳始程入京的时间就可肯定为开元十六年秋七月。而孟浩然在襄阳写《送辛大不及》一诗,亦在斯时也就甚明。又,据两《唐书·玄宗纪》记载,在唐玄宗开元年间,长安地区曾于秋季“苦雨”者凡两次,其一为开元十六年,其二即开元二十一年。现既已考知开元十六年的秋天孟浩然乃在襄阳,则是诗之作年为开元二十一年秋,乃殆无疑义[11]。
又,《年谱》于开元十六年之冬有云:“有赠袁仁敬、贺知章诗(即《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》诗——引者注),抒写落魄愤懑,表示将拂衣离开长安。”并在“按”中认为是诗题中的“袁左丞”即袁仁敬,“贺侍郎”即贺知章。按是说亦误。其原因在于:(1)检两《唐书·贺知章传》、《新唐书·许景先传》,以及林宝《元和姓纂》等材料,其中并无袁仁敬、贺知章在开元十六年前后分别任“左丞”与“侍郎”的记载。(2)《文苑英华》著录此诗“袁左丞”作“袁中丞”;而宋蜀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、元刻本《孟浩然集》于此诗题则无“贺侍郎”三字。若以《文苑英华》所载为正,则孟浩然是诗所赠者为袁中丞,但袁仁敬一生并不曾供此职;若以宋蜀刻本、元刻本孟浩然集为正,则贺知章即使在开元十六年前后任过“侍郎”一职,其也是非孟浩然是诗赠送之对象的。而或此或彼,《年谱》均不曾对其进行考证,其自说自话所结论,又焉可令人信服?所以,《年谱》系此诗于开元十六年,并以之作证孟浩然应进士举入京在开元十五年的说法,都是与孟浩然生平之历史真实迥不相及的,则其之为误,也就不言而喻。
六、关于孟浩然北游蓟门说。
《年谱》在开元十七年内,认为孟浩然曾在是年由长安北上蓟门:“新年,在蓟门观灯,有诗。”其所谓“有诗”者,指的是孟浩然集中的《同张将蓟门看灯》。并于“附考”内说:“……可见浩然并未回襄阳,而是出长安后往游蓟门。《同张将蓟门看灯》一诗,新年作于蓟门,与浩然冬季出京的经历完全吻合,看来浩然确有蓟门之游。”
按:《年谱》仅据孟浩然集中的《同张将蓟门看灯》一诗,便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的新年“在蓟门观灯”云云,实属错误。这是因为:此诗并非孟浩然所为,而是一首伪作。对于是诗之为伪作,永瑢等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孟浩然集》早已指出:“《同张将蓟门看灯》一首,亦非浩然游踪之所及,则后人窜入者多矣。”[12]此外,宋蜀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元刻刘须溪批点本《孟浩然集》,均不载此诗之实况,亦表明这是一首孟集中的伪作。而遗憾的是,《年谱》既未对此诗非伪作进行考辨,亦未指出诗题中的“张将”为何人,而仅以此诗之作年为“新年”与“浩然冬季出京的经历完全吻合”,便作出了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春曾北游蓟门之结论,这实在是太有点草率的。退一步说,即使是诗非为伪作,也是不能证明孟浩然开元十七年春曾到过一次蓟门的,因为《年谱》并未对诗题中的“张将”为何人进行具体考察。更何况,仅以此诗为依据乃属孤证,而孤证则为考证之大忌,对此,《年谱》的作者应该是十分清楚的。清楚而为之,就自应属于明知故犯,则作者所持之学术态度藉此即可见其一斑。
七、自洛之越。
孟浩然一生曾三次出游越剡,“自洛之越”乃其中之一。《年谱》因不谙孟浩然三游越剡之实况,故认为孟浩然一生只到过一次越剡,此即其系于开元十七年秋天内的“离开洛阳,往游吴越”。《年谱》并在开元二十年内云:“初春,卧疾于乐城馆中。往游永嘉,张子容有诗送行。”之后便是“五月,回到襄阳”。据此,知《年谱》认为孟浩然的此行“自洛之越”,乃始程于开元十七年秋,结束于二十年的夏五月,前后约两年又十个月的时间。
按:《年谱》此之所系为误乃,乃十分明显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:
其一,张子容自景云二年(711年)因入京赴举在襄阳与孟浩然分别后,直到开元十四年(726年)孟浩然首游越剡抵达永嘉时二人才再次相见,其间凡十五年,故孟浩然在《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》诗中乃有“平生能复几,一别十馀春”之谓。若如《年谱》所言,孟浩然与张子容再会于乐城在开元二十年(732年),其间相隔二十年有馀,按理诗应作“一别二十春”者,才与实际的情况相符,但其作“一别十馀春”而不作“一别二十春”者,所表明的正是孟浩然的这次越剡之行,乃绝非始程于开元十七年(729年)的。
其二,孟浩然集中有《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》一诗,可证开元二十年的初春孟浩然乃在洛阳,而非是在永嘉乐城的张子容府中。是诗题中的“储十二”,为诗人储光羲。孟浩然所“同”储光羲的这首“洛阳道中”,《全唐诗·储光羲集》作《洛阳道五道献吕四郎中》。“吕四郎中”即吕向。据岑仲勉《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》与《翰林学士壁记注补·唐玄宗》,知吕向开元十七年前后为主客郎中,开元十九年由主客郎中改都官郎中,则吕向可称为“吕郎中”者,至早当在开元十六年以后。又据《旧唐书·玄宗纪上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三,知开元十九年十月、十一月,唐玄宗与文武百官均在洛阳,时为都官郎中的吕向自当随驾至东都。而开元二十年,储光羲亦正在洛阳,《全唐诗·储光羲集》中有《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也》一诗,乃可为之确证。这是因为,据两《唐书·玄宗纪上》、王溥《唐会要》、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可知,信安王北伐的时间为开元二十年春正月,始程地为洛阳。开元二十年春,既然储光羲、吕向均在洛阳,而吕向斯时又为都官郎中,储光羲《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》写于是年之洛阳,即可遽断。孟浩然既“同”储光羲“洛阳道中作”诗,则其开元二十年春亦在洛阳,也就自不待言。
但需加辨正的是,《年谱》将孟浩然《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》一诗系于开元十七年二月,并以之作证孟浩然是年乃在洛阳云云,实则甚为错误。这是因为,《年谱》一则无任何材料可证吕向开元十七年乃在洛阳,二则储光羲有诗可证其开元十七年乃在安宜(即今江苏宝应)县尉任上。对于后者,《全唐诗·储光羲集》中有《大酺得长子韵》一诗,即可为证。是诗题下有注云:“时任安宜尉。”而诗题中的“大酺”,是指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其生日,诏令天下诸州宴乐并休假三日,对此,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有载,兹不具引。此则表明,《年谱》作者由于不谙储光羲生平及其诗,而导致了开元十七年储光羲“自洛之越”错误认识之产生,实为遗憾。
八、关于张明府、张郎中与张愿的问题。
孟浩然集中有《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》、《秋登张明府海亭》、《同张明府碧溪赠答》、《寒食张明府宴》、《张郎中梅园作》、《送张郎中迁京》等诗,其中的“张明府”与“张郎中”,陈贻焮《孟浩然事迹考辨》认为是孟浩然的友乡张子容[13],《年谱》在开元二十年、二十一年内则认为其乃张柬之孙张愿。《年谱》并于开元二十三年内以“附考”的形式,从五个方面对“张愿”说进行了考察,以证其说不误。
按:《年谱》的“张愿”说实可商兑。据王溥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与周一良主编《唐代墓志汇编·唐故秀士张君墓志并序》,可知张愿确曾在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任奉先县令、开元二十一年十月为驾部郎中,但此并不能证明张愿即为孟浩然诗中的“张明府”与“张郎中”。这是因为,开元二十年前的孟浩然无论是在襄阳抑或长安,均与张愿无过从关系,这从孟浩然集中无诗涉及张愿其人,即可获得明证。而张子容则不然。至于《年谱》认为“奉先令为正五品上,同书同卷(指《唐六典》卷三十——引者注)载县尉为从八品下,(张子容)迁升上如此之快,是难以想象的”云云,当为《年谱》作者未读懂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中的一段文字所致,盖因其明白写为“奉先县,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”。一个“升”字,表明奉先县令的正五品上的品阶,乃始于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,其此前则与平常之“京县”或“畿县”令等同。而据拙作《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》[14]一文之所考,张子容由永嘉乐城尉入京升任奉先县令,乃是在开元十五年春,斯时距奉先县升为“正五品上”品阶为近三年之隔。由此可见,《年谱》的“难以想象”说是很难站住脚的。又,孟浩然中的《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》一诗有云:“自君理畿甸,余亦经江淮,万里音书断,数年云雨乖。”若如《年谱》所言,“理畿甸”的“君”即“奉先张明府”亦即张愿的话,则下句 “余亦经江淮”便与事实相悖,盖因《年谱》是明确系孟浩然“离开洛阳、往游吴越”乃在开元十七年的秋天的。即在斯时,张愿尚不曾任奉先县令,孟浩然又怎么能将其说成是“自君理畿甸,余亦经江淮”呢?凡此种种,均表明《年谱》将孟浩然集中的“张明府”与“张郎中”视为张愿,是既相互抵牾,又缺少文献方面的依据的。要之,《年谱》即应以确凿的材料,以证实这样的两点:(1)张愿在开元年间的生平行事与任职经历;(2)在张愿未任奉先县令之前,孟浩然集中为什么无诗纪二人之交往?否则,《年谱》的“张明府”、“张郎中”为张愿之认识,即成为了一种想当然的空谈。
九、独孤册牧守襄阳。
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孟浩然集》卷三有《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》一诗,其中的“独孤使君同”,乃“独孤使君册”之讹。《年谱》则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一年,以表明独孤册牧守襄阳,即在是年前后。
按:《年谱》此之所系,实则大误。考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七《目录七·唐》有《唐襄州牧独孤册遗爱碑》,注云:“李邕,萧诚行书。是碑又见《集古录》跋尾七:“右独孤府君牌……在岘山下。……府君讳册,字伯谋,河南人,尝为襄州刺史。此碑襄人所立也。” [15]独孤册任襄州刺史期间,因与孟浩然过从甚密,故孟浩然乃有《陪独孤使君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》一诗。除此诗外,《孟浩然集》卷二另有《同独孤使君东斋作》一诗,以纪二人在襄阳之过从。是诗有云:“郎官旧华省,天子命分忧。襄士岁频旱,随车雨再流。云阴自南楚,河润及东周。廨宇宜新霁,田家贺有秋。”考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云:“开元十四年秋,诸道州十五旱。十五年诸道州十七旱。”此则可证,《同独孤使君东斋作》一诗当写于开元十五年秋天,而独孤及牧守襄阳自当在开元十五年前后,也就可以肯定。王士源《孟浩然诗集序》载云:“丞相范阳张九龄……太守河南独孤册,率与浩然结忘形之交。”则独孤册与孟浩然“结忘形之交”者,乃在开元十五年前后之襄阳,也就不言而喻。所以,《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》诗之作年,非如《年谱》所系为元二十一年,即乃甚为清楚。
十、关于入蜀问题。
《年谱》在开元二十三年云:“浩然入蜀,往游广汉,陶翰作序相送,其事殆在本年冬。”并有“按”云:“据陶翰此序(指《送孟大入蜀序》——引者注),浩然入蜀,在开元十六年游长安之后,而以浩然生平考之,除本年外,浩然皆不大可能入蜀,故系于此。”
按:《年谱》对于孟浩然入蜀时间之所系,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。其一,陶翰《送孟大入蜀序》无只字表明“浩然入蜀,在开元十六年游长安之后”,而《年谱》此之所言,则纯系自说自话,未可信之。同此者,另有“除本年外,浩然皆不大可能入蜀”云云。第二,据上引拙作《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》一文所考,开孟浩然元二十三年乃在其第三次越剡之游的途中(详前),他根本不可能自襄阳“入蜀,往游广汉”。第三,陶翰在何时何地与孟浩然相交,其《送孟大入蜀序》又写于何时何地,《年谱》对此均无只字相及,其又何以可证孟浩然的入蜀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呢?而事实上,孟浩然的入蜀乃在开元十二年秋,始程地则为长安而非襄阳。
据陶翰《送孟大入蜀序》一文之所载,可知孟浩然此行之入蜀游,乃是由川北(“广汉”)南下而“西入岷峨”的,则其此行始程地为秦咸一带,即甚为清楚。对此,孟浩然集中的《途中遇晴》一诗,又可为之佐证,是诗有云:“已失巴陵雨,犹逢蜀坂泥。”诗中的“巴陵”,方回《瀛奎律髓》、毛晋汲古阁本《孟浩然集》,均作“五陵”,按作“五陵”是。“五陵”在长安。这两句诗是说,孟浩然在长安始程为雨天,待进入蜀境时虽已转晴,但仍是“坂泥”难行。考孟浩然一生三入长安(第一次在开元十一年冬至开元十二年七月前后,第二次在开元十六年秋至开元十八年底,第三次为开元二十年冬至开元二十一年秋),由秦经蜀还襄阳者只有开元十二年秋天的这一次[16],则其之入蜀,非如《年谱》所系为开元二十三年者,即乃甚明。
《年谱》除了以上所考辨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外,还存在着诸多可供商榷之系年,如认为卢僎为襄阳令始于开元十二年,与张郎中、孟浩然在襄阳唱和的“卢明府”为卢象,以及孟浩然与崔国辅、宋鼎等初识的时间,李玭再封义王之确时,等等,即皆为错误而需作重新考察。而特别是在一些“系年诗”内对孟浩然诗的系年,误系者则更为严重。凡此种种,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《年谱》的学术价值。之所以如此,主是是作者表现在两个方面的不足:一是涉猎典籍有限,二是文献学功底欠缺。
来源:网易新闻·网易号“各有态度”特色内容
